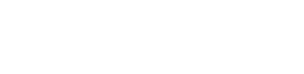他是一位核医学专家,系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。这十年间,他曾开过自己专业以外的深受医学生青睐的两门课:一门是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时开设的《名画中的医学》,另一门是现在担任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时开设的《名画中的瘟疫史》。
他就是黄钢教授。他说:“我曾冥思苦想,试图以一种柔和而不生硬的、一种润物无声而不是灌输式的办法,来启迪、诱导、感化在校的医学生,使他们将来穿上白大褂真正成为一名医生之后,能多一份爱的情愫。特别是在疫情发生后,更要让医学生们知史明史,从名画共情历史。”

名画中的医学韵味
2011年开始,黄钢开了一门名为“名画中的医学”新课,试图“解码”那些名作中的疾病和医学现象,捕捉当今医学教育中可能正在丧失的人文传统。尽管他的课有时被安排在晚上,但偌大的演讲厅还是被挤得满满的。医学生们在聆听后都十分感叹:“第一次陶醉在艺术与医学紧密结合的浓烈氛围中,在名画中感受到了医学的另一种魅力。”
当时,在黄钢的办公室里就挂着路克·菲尔德斯的名作《穆瑞医生》。黄钢说,他很欣赏世界名画,尤其酷爱这幅。画作讲述的是,经历了一夜抢救,患病的孩子似乎脱离了危险,但疲惫的医生仍然坚守在床边。他手托下巴,全神贯注地看着孩子,似乎在思考下一步的处理方案。画面构图美妙而富有动感,孕育着丰富的故事及想象空间,表现出艺术与医学及人文的精妙融合,透射出医患之间的崇高信任与性命相托。

“《穆瑞医生》中那种融洽、和谐的医患关系,一直是我期盼并努力追求的。然而,这些年来,我们的医院似乎更多地强调了先进的诊疗技术,而流失了人文关怀。但医学是人的科学。离开人,医学就失去了本源;离开了人文关怀,医学就失去了灵魂。所以,我希望我的学生能体会到作为医生的伟大及其奉献精神。”黄钢说,他对世界名画感兴趣,源于1991年赴法国约瑟夫·傅里叶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时。
当时,来到慕名已久的巴黎参观卢浮宫,黄钢对卢浮宫陈列的世界各国名画流连忘返。尤其看到与医学沾边的名画,他更是如痴如醉,常常清晨就背着一根长棍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排队入场,直到傍晚时分才离开。画作背后那种对理性的追求、对人文的关注、对科学的执著,从那以后,便时常撞击在黄钢心头。
“近几年,我曾冥思苦想,试图以一种柔和而不是生硬的、一种润物无声而不是灌输式的办法,来启迪、诱导、感化在校的医学生,使他们将来穿上白大褂真正成为一名医生之后,能多一份爱的情愫。出于原先对世界名画的热爱,我首先想到了当年曾震撼我的世界名画,想借鉴名画中的医学韵味,通过讲座的形式来潜移默化地熏陶莘莘学子。”
在课堂上,黄钢展示的表现医师敬业精神的名画,如杨·斯特恩的《生病的夫人》、弗朗西斯科·戈雅的《阿雷塔大夫与我在一起》等,其中并没有太多的医疗器械,也没有惊心动魄的诊治场面,但那情同手足的关爱画面,足以震撼所有人的心灵。

《阿雷塔大夫与我在一起》
黄钢说:“画中的年代,虽然没有今天的抗菌药物及先进设备,大量患者因患上在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病症而失去了生命,但医生用他们的真诚关怀、爱心奉献及竭力挽救生命的努力,获得了病家的信赖。希望这些埋藏于世界名画中的医学点滴,能引燃医学生探索科学的热情,让医学变得妙趣横生。”
“永远不要轻视医学的力量”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,黄钢已在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任上5年。除了进行一些讲座或座谈外,他又萌生了一个新念头——在全球性疫情中,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?于是由他主讲、面向全国高校开设的包含40多节微课的《名画中的瘟疫史》在线开放课程。通过师生的共同探讨,黄钢试图对上面的问题作出回答。
黄钢说:“世界上每一次大瘟疫都深刻影响战争的走向、文化的兴衰与社会的变迁,保留灾难记忆绝非为了沉湎于苦难哀痛,而是从中学习、反省,从而获得成长和改变的力量。由我担任总策划的在线开放课程而印刷出版的《名画中的瘟疫史》以画说史,鉴古知今,已经成为世界慕课大会主视频的宣传内容和推荐课程。”
“从《名画中的瘟疫史》的画册中可以看到,在整个地球的瘟疫史上,画家们始终用自己画笔忠实地记录着艺术的真实。” 黄钢指出,艺术本质上都是在表现画家自己及其内心,以此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共情、与社会现实的共鸣、精神世界的共振。
从《被遗忘的流行病“世界大战”:1918大流感》《死神的胜利:黑死病》《雅典大瘟疫》《东北大鼠疫》《中华瘟疫史画》到《医学变革和公共卫生发展——我们能从疫情危机中获得成长和改变的力量吗》收尾,黄钢的课程总共六章、40多节微课。
黄钢说,他尽力使自己的课程内容和形式并举,重视音乐、画面、剪辑等要素,用今天学生易于接受的形式传递内容。通过这些课程,他希望医学生们:“永远不要忽视生命的脆弱,永远不要低估自然的野蛮,永远不要轻视医学的力量。”
原文地址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Q4KzZ7IHB5qwhdckMwdmXg
实习编辑:李雪凝